馴獸館內的表演對於朱文奎來說絕對可謂之新鮮,是他在南京皇宮裡從未曾看到過的。
那些曾經被世人畏懼,視為兇猛的野獸,獅虎熊豹在一個個馴獸師鞭子的指揮下,進行著一項又一項的表演。
「畜生也會這麼聽話?」
扶著二樓平台的欄杆往下看,朱文奎不懂,倒是一旁守著的夥計給介紹了一下:「這些猛獸您別看塊頭大的嚇人,其實在還是小崽子的時候就被開始訓練了,所以經過這麼多年的馴服,比起咱們尋常百姓家裡養的貓狗都差不多,骨子裡早沒了野性。」
靜靜的看著,看著被譽為叢林之王的獅虎乖巧如哈巴狗一般,朱文奎突然感慨了一句。
「萬物皆有靈,將一隻猛獸變為家畜,怕是從小沒少打吧。」
馬玲看了幾眼之後,也覺得有些沒勁,那些四周叫好鼓掌的觀眾讓她覺得厭惡。
「就是因為這些人願意看,才間接讓這些猛獸遭了殃。硬生生將一隻猛虎變成狗,這太殘忍了。」
生性追逐自由嚮往自由的馬玲,實不喜歡這種畫面。
「我現在都不敢想像,如果將來有一天被我爹強迫著出閣嫁夫,從此被鎖在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深宅之中,那該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」
這句話恰恰說道了朱文奎的心裡,他嘆了口氣。
「是啊,你我兩人,在人生的大事面前,哪有自己真正做主的機會。」
看看這些乖巧馴服的獅虎,這一刻,馬玲和朱文奎不知道為什麼就聯想到了自身,感觸萬千。
蒼鷹折斷了翅膀,那還叫飛禽嗎。
四周坐著的陳昭等人都不知道該怎麼接話,只好眼觀鼻鼻觀心的沉默著。
反而在朱文奎等人的隔壁一處看台,一名倚著欄杆觀看的男人側過頭,不屑的哼了一聲。
「你倒是菩薩心腸,管的挺寬啊。」
「大膽!」
「放肆!」
幾名錦衣衛厲喝出聲,便是連陳昭等人都嚇的小臉一白。
反倒是朱文奎不以為意的抬手,揮退了幾名前跨幾步,準備尋這男人麻煩的錦衣衛,好笑的反問一句。
「難道鄙人說的有不對之處嗎?還是說這位兄台有什麼高見。」
馬玲脾氣要更火爆,站起身杏目瞪著這個口出狂言的男人:「本姑娘倒想聽聽你狗嘴裡能吐出什麼象牙來。」
「放肆。」
男人的身後同樣站著幾個護衛,聽到馬玲這般毫無禮貌的話語頓時著惱,齊齊喝了一句,這一下,頓時讓平台之上的氣氛劍拔弩張起來。
這可把兩邊陪著的夥計嚇得夠嗆,心裡不住的念叨千萬別打起來,但雙腿卻完全嚇得僵住,根本邁不開。
這男人三十來歲,對馬玲這般呵斥倒也不惱,只是輕蔑的笑了笑。
揚手,示意身後的護衛退下,開口。
「這些畜生有什麼好心疼的,它們固然失去了自由和本性,但也因此獲得了安定和飽餐,不用整天想著狩獵餓肚子,更不用擔心被其他更兇猛的野獸獵殺。
失去和獲得總是相對的,我看你倆歲數不大,但氣度尊貴,說明家裡面有官吧。
回去問問令尊,做官好不好做,每天要說多少違心的假話,帶多少不同的面具。
連我們人都活不成自己想去活的樣子,倒還有閒情來心疼這些畜生了?」
朱文奎頓覺面頰發麻,心生震撼。
好一句連我們人都無法去活成自己想活的樣子。
同朱文奎的沉默不同,馬玲則更是不屑,反唇相譏。
「你倒是說的一口無知之語,我父親為人還真不像你說的那般虛偽,他可是頂天立地的英雄,行的堂堂正正。
本姑娘自幼也是率性而活,還真不看別人臉色。」
「呵呵。」男人懶得回應馬玲,轉身欲走,被朱文奎喊住。
「兄台之語可謂振聾發聵,敢問兄台尊姓大名。」
男人立住,而後側首。
「免貴姓李,區區薄名不值一提。」
李姓男人回了座去飲酒,馬玲切了一聲:「故弄玄虛。」
第五百七十一章:BJ(五) 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 末世大回爐 喪屍爆發,人類絕境來臨,地球磁場瞬變,一切回歸最初,回到原始。 末世,我來了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初級1群:424355442(已滿)。 初級2群:582138519。 正版VIP群
末世大回爐 喪屍爆發,人類絕境來臨,地球磁場瞬變,一切回歸最初,回到原始。 末世,我來了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初級1群:424355442(已滿)。 初級2群:582138519。 正版VIP群 天國遊戲暫時無小說簡介
天國遊戲暫時無小說簡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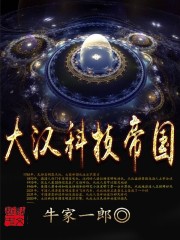 大漢科技帝國 (新書宇宙霸業已經很肥了,可以開宰了,番外篇也會放在新書的作品相關) 我們改造星球用來移民; 我們在太空中發展農業、興建工廠; 我們在小行星帶,柯伊伯帶開採資源; 太陽系就是我們的後院
大漢科技帝國 (新書宇宙霸業已經很肥了,可以開宰了,番外篇也會放在新書的作品相關) 我們改造星球用來移民; 我們在太空中發展農業、興建工廠; 我們在小行星帶,柯伊伯帶開採資源; 太陽系就是我們的後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