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嘿!我這暴脾氣嘿!」
蒸騰著水汽兒的淋浴室里,陸堯擠出一坨洗髮水,不由分說的抹在了衛燃的腦瓜頂上,「哪的人吶?」
「滄洲的,我叫衛燃。」
衛燃也沒拒絕對方的好意,一邊將頭頂的洗髮水揉搓出泡沫一邊反問道,「首都人?」
「啊,可不。」
陸堯一邊搓著頭上的泡沫一邊壓低了聲音問道,「哥們兒,你真從前線下來的?」
「你咋知道的?」衛燃笑著反問道,「就憑我頭髮長?」
「你的背囊和餿了的大衩兒就在外面放著呢」
陸堯遠比衛燃以為的要更加細心,「鋼盔上帶著偽裝,槍托上有紅土泥,肯定從前線下來的沒跑了。」
說到這裡,陸堯往後退了一步,指著另一邊正在試圖將頭上的洗髮水泡沫塗抹全身的小西鳳說道,「他是賀勇,寶雞人,叫他小西鳳就行。」
「小西鳳?」
衛燃心頭一動,抹了一把臉好奇的問道,「這外號怎麼來的?」
「額答是西鳳酒廠的工」
「普通話,小西鳳,你都是個通信了,你得說普通話。」陸堯幫著糾正道。
小西鳳,或者說賀勇抹了抹臉上的水漬,一邊用剩餘的泡沫揉搓著咯吱窩一邊憨笑著解釋道,「我爹是西鳳酒廠的工人,我參軍的時候,我爹給我偷偷裝了兩斤西鳳酒路上喝。」
說到這裡,小西鳳一臉懊悔的說道,「我在火車上偷著喝酒的時候被接我們的首長發現了,我還把他給灌趴下了,等快到站了才知道那是副師長。」
額.
衛燃咧咧嘴正要說什麼,刀班長也已經拿著一條毛巾走了進來。
「班長」已經洗的差不多的衛燃主動打了聲招呼。
「洗完了快去剪頭髮」刀班長催促道,「咱們時間不多」
「是!」
衛燃再次應了一聲,和陸堯以及賀勇各自點了點頭,沖乾淨身上最後一點泡沫之後,一邊用毛巾擦拭著一邊走出了淋浴室。
換上背囊里那套全新但卻難免帶著霉味的綠軍裝,衛燃將胸掛、水壺步槍乃至那條自製大褲衩和舊的解放鞋等物全都塞進背囊,小跑著鑽進了隔壁的理髮室。
「同志,來這裡坐。」
這理髮室里,一個看著能有30歲上下,走路一瘸一拐的男人一邊招呼著,一邊用力抖了抖圍布。
「謝謝」
衛燃依著對方的吩咐坐在小凳子上,任由那位理髮師給自己罩上了圍布。
「怎麼剪?」這理髮師傅拿起手推子的同時問道。
「越短越好,但是不要光頭。」衛燃想都不想的答道。
「回前線?」這理髮師傅一邊給推子滴上些許潤滑油一邊問道。
「你怎麼知道?」
衛燃好奇的問道,這師傅既然用的是「回」而不是「去」,顯然是有著足夠的把握做出的如此猜測。
理髮師傅笑了笑,卻並沒有說些什麼,只是操作著手推子,用梳子墊著,僅僅只用了五分鐘,便幫他剪掉了略長的頭髮,順帶手,還幫他把鬍子給颳了刮。
直到將一條熱毛巾遞給衛燃示意他擦擦脖頸處的碎頭髮,這理髮師傅才回答了開始的問題,「我也是從前線下來的。」
不等衛燃說些什麼,同樣換了一身乾淨軍裝的刀班長也走進了理髮室。
將位置讓給了對方,衛燃也沒急著離開,自顧自的從包里翻出那支78壺,將裡面並不算多麼乾淨的水倒掉,又湊到水龍頭的邊上仔細涮了涮,重新接滿了乾淨的自來水。
趁著刀班長理髮的功夫,他安靜的坐在了靠牆的長椅上打量著這理髮室里的布置。
除了幾個人均身有殘疾的理髮師傅之外,讓他尤其注意的,便是掛在牆上的日曆。
在這日曆上,顯示的時間是1984年的3月25號,是個周末,陽光還算明媚的周末。
暗暗將這個時間記在心裡,他又借著背囊的掩護取出金屬本子裡的指北針,將另一面的飛返表對照著牆上的掛鍾,把時間調整到了下午四點16分。
他這邊一番磨蹭,刀班
第1384章 整裝待發 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 都市兵王暫時無小說簡介
都市兵王暫時無小說簡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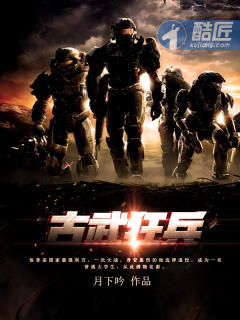 古武狂兵 他曾是國家最強利刃,一次大戰,身受重傷的他選擇退役,成為一名普通大學生,從此潛隱花都。
他身懷古武絕學,暴打權貴惡徒,你狂,他比你更狂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古武狂兵》還不錯
古武狂兵 他曾是國家最強利刃,一次大戰,身受重傷的他選擇退役,成為一名普通大學生,從此潛隱花都。
他身懷古武絕學,暴打權貴惡徒,你狂,他比你更狂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古武狂兵》還不錯 特種兵在都市 楊洛曾經是一名讓所有國家軍人聞名喪膽的兵王,他是地下世界大名鼎鼎的殺手法官,他是世界醫學界裡天才醫生,他掌握着神秘組織高買。他性格囂張狂妄,為達目的不折手段。他痞氣十足,各種美女為他痴狂。在這
特種兵在都市 楊洛曾經是一名讓所有國家軍人聞名喪膽的兵王,他是地下世界大名鼎鼎的殺手法官,他是世界醫學界裡天才醫生,他掌握着神秘組織高買。他性格囂張狂妄,為達目的不折手段。他痞氣十足,各種美女為他痴狂。在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