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後,在廣場東方酒店的餐廳里,四個三十出頭的壯年人聚在一起。
多出來的,是委託人的妻子,因為一切已經妥善安排,她也被林義龍建議和委託人一塊出行。
「太感謝你了。」委託人說道。
「這也算把年關熬過去了。」林義龍答道,「明天準備一下,開始新生活吧。」
四人把盞言歡,林義龍的新客戶已經在青年旅社中支撐了近一個月,不能總是在雙慶大廈的青年旅社久住。有更多的手續需要這位先生去目的地辦理,經過一些勸說,他和妻子坐明天凌晨的飛機離開。
「我父母那裡,不會有什麼牽連吧?」
「有什麼牽連,都是退休人員,還能不發退休金還是怎麼著?」林義龍反問道,「不用擔心,等幾周後,你們一家就團圓了。但面試時一定要見機行事,咬緊牙關堅持。」
「也好。」委託人答道,「再次感謝你。」
委託人夫婦吃了兩筷子菜/兩勺湯那麼意思意思,幾個人就相互道別,分道揚鑣。
因為委託人是許振坤關係更好,林義龍留在座位上繼續吃,由許振坤把他們送出餐廳。當他回來的時候,只見桌上殘羹冷炙已經被清理掉了,服務員端上了火鍋鍋底,同時又端上潮汕牛肉,放在一旁。
「你胃口真不錯。」這兩天,許振坤都在陪委託人回答林義龍提出的各式各樣的問題,幫助林義龍和他的合伙人審查文件,林義龍每天飲食異常節制,每天的熱量來源只是兩個花生醬三明治和三杯咖啡。就在以為林義龍徹底改食譜成為素食動物的時候,沒想到他竟然沒吃飽一樣開始吃起潮汕牛肉火鍋來——只是,他的蘸料是經典的燕京麻醬,而非沙茶醬。
「終於能吃點東西了!」林義龍如釋重負一般地跟許振坤說道,仿佛又恢復成許振坤中學時期的樣子,「我整整糾結了三天,總算弄出點眉目來了。」
「什麼意思?」許振坤摸不到頭腦,但有一點確信,林義龍永遠不可能提及證件和入境的問題。
「我想知道他在你這裡投了多少錢?」林義龍問道,「我來猜猜,五百萬AUD?」
「你怎麼知道的?」許振坤問道。
「既然能讓你這麼重視,金額肯定低不了,比我『湊份子』一樣的小打小鬧肯定是高太多了。」林義龍給出了他的分析,「所以,至少10倍於我的投資才能讓你在大年夜把我從倫敦拖到這裡。要不然我只能說,我們的友誼是玻璃的。」
「行吧,跟這個數也差不多。」許振坤答道,「雖然猜得數字有些出入,大概數額也差不離。」
「我對具體的數字毫無興趣,關鍵是我懷疑他能不能付清我們的費用。「林義龍說道,」單單我這裡,大概就需要15萬澳元律師費、他還要在國外買房子置產,粗估一下又是將近70萬澳刀,你的基金又是相對封閉的,幾乎不可能終止委託,那麼問題來了——他上哪兒弄那麼多真金白銀去?「
「你是說?」許振坤才意識到好像哪裡出了問題,他慌忙坐到林義龍的對面。
「你知道我想說什麼。」林義龍給許振坤的碗裡裝滿麻醬,「我們來算算,一個創業公司創始人,父母都是退休了的上班族,是如何在幾年之內擁有超過三千萬軟妹幣的現金的?」
「什麼,退休的上班族!」許振坤叫道,「他父母不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商人嗎?」
許振坤不由得有些擔憂。他知道創業後能挺過前兩輪風投的項目幾乎百不存一。就算是毛利潤相當高的製藥行業,也不可能在初創公司就能有幾千萬的緊張。很有可能所謂的「小股東」都是像他退職之前那樣的投資經理,都是融資圈的熟人。
換句話說,其實許振坤的這位同學的罪行幾乎是確鑿的,而且投入資金時沒跟他說實話。
「他是你的朋友,我沒話說。」林義龍涮著牛肉,頭也不看自己的好友地答道。
「那你怎麼辦?」許振坤問道。
「我無所謂啊!」林義龍沒好氣地說道,「我的收費只關於他的財產信託的,他要是出了問題我盡到了義務也不能退這筆諮詢費。我直接從你這邊直接拿封閉份額就行。」
說著,林義龍從錢夾里掏出一張基金份額的轉讓書給
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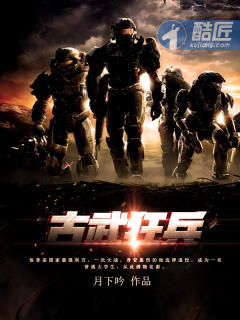 古武狂兵 他曾是國家最強利刃,一次大戰,身受重傷的他選擇退役,成為一名普通大學生,從此潛隱花都。
他身懷古武絕學,暴打權貴惡徒,你狂,他比你更狂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古武狂兵》還不錯
古武狂兵 他曾是國家最強利刃,一次大戰,身受重傷的他選擇退役,成為一名普通大學生,從此潛隱花都。
他身懷古武絕學,暴打權貴惡徒,你狂,他比你更狂!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古武狂兵》還不錯 都市兵王暫時無小說簡介
都市兵王暫時無小說簡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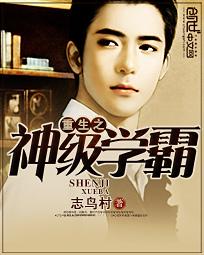 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
重生之神級學霸 生物系研究僧出身的猥瑣胖子楊銳,畢業後失業,陰差陽錯熬成了補習學校的全能金牌講師,一個跟頭栽到了1982年,成了一名高大英俊的高考復讀生,順帶裝了滿腦子書籍資料 80年代的高考錄取率很低?同